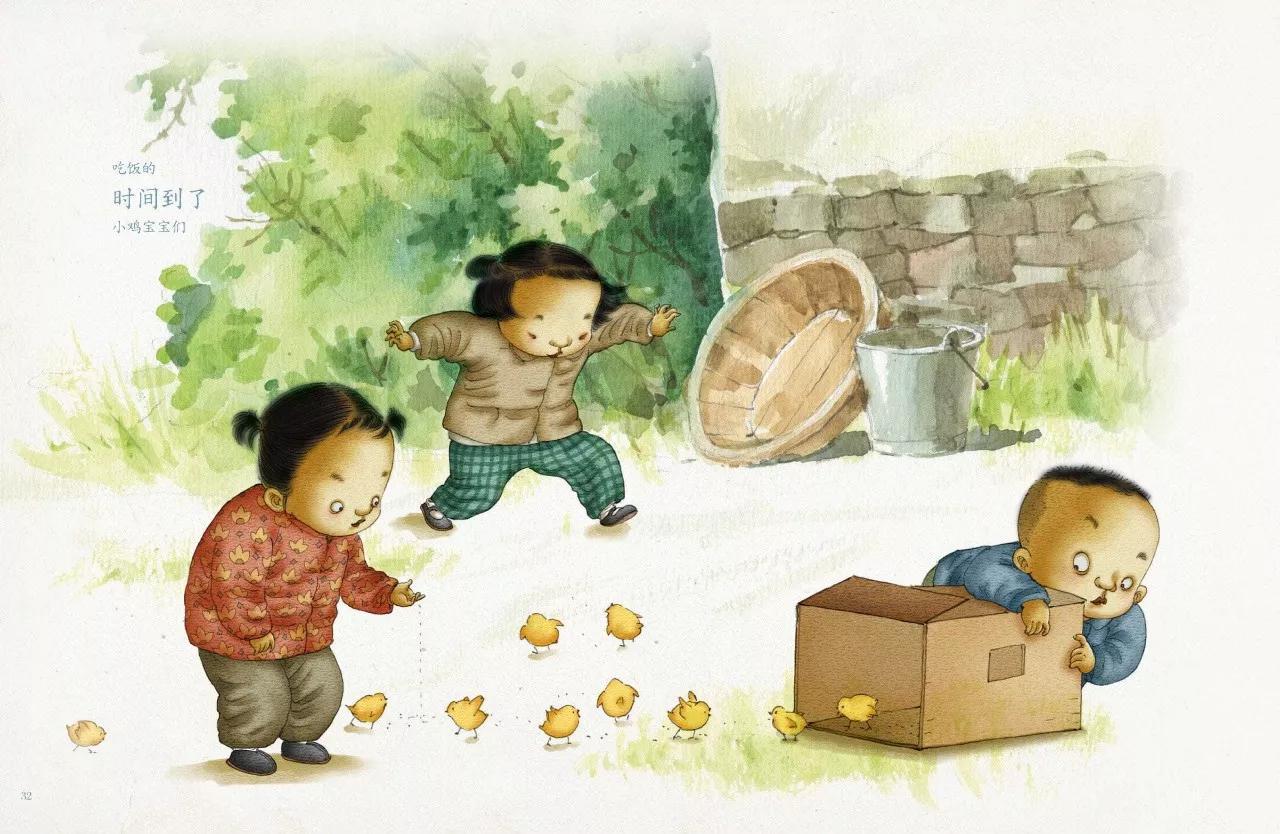
当清冷的秋风携着细细的秋雨,又一次来到大地之时,空气顿时变得湿润起来,风儿时不时带走一片片飘零的黄叶。看着那些随风起舞的落叶,它们从高处与世无争的轻落下,却还是去为自己的根系增添肥力。此时此刻,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又想起姥姥了。
年少时,父母工作繁忙,家里人口多,全凭父母微薄的工资养活我们全家五口人,上世纪八十年代,日子过得很清苦。似乎连过年在家里吃什么都已经忘记了,可是唯独还记得七八岁时,暑假里在姥姥家吃炸拖罗的事。那时无论我们去姥姥家有多勤便,姥姥总是笑眯眯地欢迎我们姐妹俩以及一大群外甥们,炸拖罗的事就被正式拿上了议事日程。只要一看见姥姥洗完手,拿起她的那个宝贝的白底漆着红色花纹的大瓷盆,我就兴奋得合不拢嘴,我知道姥姥又要拿出她的绝活炸拖罗来盛情款待我们了。这个时刻,就算是外面的知了叫得再欢,就算是兄弟姐妹们有什么新鲜的小玩意喊着让我一起观赏或玩耍,我是一概不管不问的,此时我小小的心里,被姥姥炸拖罗的事占着满满的,实在没有空去管其他的事情了。
我像个跟屁虫跟在姥姥身后,认真看着姥姥的每一步操作,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小细节,生怕会晚一秒吃到了姥姥炸的金黄、闪亮、香气扑鼻的拖罗。只见姥姥先舀了大半盆面粉在盆里,然后拿起开水瓶,将早上烧的滚烫的水轻轻倒进面粉里,然后拿起筷子迅速地搅拌,姥姥一边快速搅拌,一边观察面是否烫熟了。听姥姥说,这烫面是很关键的一步,面烫不好,炸出来的拖罗就不好吃。姥姥一边烫一边搅,一边根据面粉的干湿来缓缓地加开水,直到这面粉像听话的孩子达到姥姥的标准干湿合适,姥姥才把它们放在洁白的案板上,然后进行下一步准备工作。
她又走到客厅里,打开柜子,拿出一个袋子提到厨房里,姥姥把袋子里的白芝麻倒进一个水瓢里,把它们洗干净沥干。接着,在土灶里放上松毛小火,等锅内的温度正好时,把芝麻放进锅里慢慢地炒着。不多会,厨房里就冒出一大阵的香气,我使劲吸着鼻子,口水都有些往下流了。姥姥把炒熟的芝麻盛在一个大号的搪瓷盆里,等它们冷却后又拿来白糖跟芝麻混合好。做完这些,姥姥去用手试了试面的温度,觉得已经不那么烫了,她又用手把面和匀实。虽然面不是很烫,我看见姥姥的手还是被烫红了。我很心疼,抓住姥姥的手,放在我的嘴边吹着,姥姥又怕我累着了,又想快点让我吃上拖罗,还没吹两下,她就不让我吹了。我只好搬来一张小椅子,坐在厨房的墙角边看着姥姥继续干活。
最精彩的一幕马上就要上演了,这会,我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。外婆先拿来两个面积有篮球那么大的圆形白瓷盘,然后,揪了一团面,把它揉成一个圆团,不多大一会,面粉都成了面团乖乖地呆在瓷盘里。接着,外婆拿出她的小檊面杖,再把一个个面团檊成圆形的厚薄适中的面皮,我最喜欢的环节就要来了,只见姥姥把炒好的芝麻放进她的大面皮里,还在四周叠成一个个小小的褶子,就像小姑娘穿着的荷叶裙边,真是极其好看的,包完了拖罗,这算是完成了一大半的,下一步,就是要炸拖罗了。
姥姥一个上午都没有歇息,一直都在做着拖罗。当灶内的火花噼啪作响,红红的火光映着外婆淌满汗水的脸时,那一刻,我感觉有外婆真好,我真幸福。此刻,外婆用毛巾擦了一把汗,又洗了一次手,才把自家种的菜籽油倒了大半在锅里,当锅内油温渐高,菜油们在锅里跳起欢快的舞蹈,翻腾起星星点点的油泡,就是拖罗要进到锅里给自己“镀金”的时刻了。姥姥拿起包好的拖罗,一个个轻轻的顺着锅边放进锅里,伴随着油温的升高,随着拖罗由生到熟的转变,一阵更好闻的香味弥漫了我的全身,那是菜油的醇香,夹杂着芝麻经过高温后迅速分解的香气,我感觉那香味肯定能传到几公里以外。
拿起一个拖罗放在手里时,我从来不舍得一下就把它咬坏,总是先细细的端详了之后才放进嘴里,那拖罗金黄中透着些少许的深红色,一个个圆鼓鼓的,好像一个个凯旋归来神气活现的大肚将军,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外面的褶子又香又焦,里面的芝麻馅又香又甜。咬一口拖罗,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小时候,我觉得吃拖罗的感觉真的比过年的感觉还要好。姥姥总是用她的一双巧手,不辞辛苦地改善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既享受到美味佳肴,又改善了我们的生活。
现在每天在外面过早时,都会看到市面上卖的有炸拖罗,我却再也没有买过了,只因为我曾经品尝过姥姥做的最美味的炸拖罗,如今我勤劳善良、可敬可爱的姥姥,已经离开我近四年了,对姥姥的思念却从没有停止过,当窗外的阵阵秋风带走一片片枫叶翩翩起舞,当我们一大家子在夜晚围坐在电视机前谈天说地时,我常常想,如果姥姥在该有多好啊!
望着窗外飘落的黄叶,回忆姥姥曾经给予我的爱,我眼眶发热,姥姥,我也将把善良的种子馈赠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

